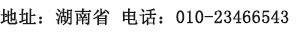夏洛克·福尔摩斯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破案的手段,更是一整套思维方法……它脱胎于科学方法,但又超越了科学与犯罪,自成为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生存之道。甚至,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功用与在柯南·道尔的时代一样强大。——玛丽亚·康妮科娃
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
一年前,美国学者本尼克特·安德森在清华访学,我千里迢迢跑去听他演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提到自己从小喜欢读《福尔摩斯》,而且一直记得福尔摩斯对华生说过的一段话:“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不要看你能看到的,要看你看不到的。”
这句话对他日后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看你能看到的东西,但是首先你得思考这里是不是少了什么。”比如,他在研究泰国的华人社会时发现,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同派别之间用语相当粗鄙难听,但从来没有出现的那一个词——“jek”(本意是海外华人)。他对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
安德森教授的故事给我很大的启发,也让我对“观察”这件事情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为什么福尔摩斯在轻轻一瞥眼之间就能洞悉各种秘密,而我们眼睛睁得再大都发现不了一点端倪?福尔摩斯式的观察力到底从何而来?
不久前,我读到一本叫《福尔摩斯思考术》(Mastermind:HowtoThinkLikeSherlockHolmes)的书,作者叫玛丽亚·康妮科娃(MariaKonnikova),一个俄罗斯裔的美国女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心理学博士。她在前言里说,自己小时候听父亲讲福尔摩斯的故事,就深深为福尔摩斯那颗奇妙的大脑所着迷,等她长大后,重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时,惊奇地发现这位19世纪侦探关于破案的一套思维原则与21世纪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发现不谋而合。比如,福尔摩斯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说:“人的脑子就像一间小小的空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把一些家具放进去。”
《福尔摩斯历险记》剧照()
就人的记忆机制而言,“阁楼”的比喻是很有道理的——“当我们看某样东西时,它首先要经过大脑进行编码,然后才会被存入海马体。海马体可以被视为阁楼的首个入口。在你知道自己是否会调用它之前,你就已经把自己知道的每样东西都放在其中了。以此为起点,以往即有的经验和以前的选择(比如你通常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为基础,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或者你的大脑认为值得存储的材料将被转移到阁楼里的某个特定的盒子里,装进一个特定的文件夹,处在一个特定的大脑皮层——阁楼存储空间,也就是你的长期记忆的隔间里。这就是记忆巩固的过程。当需要回想起某个特定的记忆时,你的大脑会立刻找到正确的文件夹,并把它提取出来。有时,它也会抽出相关的文件夹,激活整个盒子里的内容或者附近发生的所有事件,即联想激活。但是,这个提取的过程充满了变数。”
福尔摩斯的大脑阁楼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中给福尔摩斯的学识范围开列了一张颇有意思的简表:
1.文学知识:无。
2.哲学知识:无。
3.天文学知识:无。
4.政治学知识:浅薄。
5.植物学知识:不全面,但对于莨蓿制剂与鸦片却知之甚详,对毒剂有一般的了解,而对于实用园艺学却一无所知。
6.地质学知识:偏于实用,但很有限,但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他在散步回来后,能把溅在裤子上的泥点,根据颜色和坚实程度说明是在伦敦什么地方溅上的。
7.化学知识:精深。
8.解剖学知识:很准,但无系统。
9.惊险文学:很广博,对近一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都深知底细。
10.提琴拉得很好。
11.善使棍棒,精于刀剑拳术。
12.关于法律方面,具有充分实用的知识。
这些只是华生在刚认识福尔摩斯时记录的。在之后的合作中,这位大侦探渐渐透露出更广博的知识面,比如他至少懂拉丁文、德语和法语三门外语,他偶尔会引用拉丁文,或是用法语说话。在《血字的研究》里,他一眼就认出了Rache是德语中“复仇”的意思。
他具有丰富的犯罪学的知识,比如他对烟草和烟灰的研究极为细致,曾经写过一篇叫《论各种烟灰的辨认》的论文,列举了多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还用彩色的插图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比如“印度雪茄烟的黑灰与‘鸟眼’烟的白灰的不同,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就像白菜和马铃薯的区别一样分明”。
他能辨识75种香水的不同味道。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庄园主人亨利收到一份匿名便条,催促他离开巴斯克维尔庄园。福尔摩斯从便条里闻到一种白迎春花的香味,正是从这股香味中,他意识到案子牵涉一位女士。
区别报纸所用的铅字字体,在福尔摩斯看来,也是犯罪学专家最基本的知识之一。他能一眼从一封神秘来信中辨认出《泰晤士报》的小五号铅字,并从中得出了许多线索,包括写信人的教育背景、写信的地点,以及写信时的心情等等。
在《四签名》中,他充分展示了利用脚印或是车轮痕迹来寻找犯罪线索的能力。
在同一个故事里,他还提到自己写过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可以影响他的手形,附有石工、水手、木刻工人、牌子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的手形插图。
福尔摩斯还懂得一些心理学,在《波西米亚丑闻》中,他用一个小伎俩就成功地让爱琳阿德勒泄露了照片隐藏的位置。在《身份案》中,他甚至就恋爱中的女人的行为模式发表了一番高论:“在人行道上犹犹豫豫通常是意味着发生了桃色事件。她想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但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把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当一个女人觉得一个男人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情时,她就不再犹豫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把门铃线都给你拉断了。”
《神探夏洛克》剧照
华生唯一一次惊叹于福尔摩斯的“无知”,是发现他对于哥白尼学说以及太阳系的构成一无所知——“当此19世纪,一个有知识的人居然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运行的道理,这件怪事简直令我难以理解。”
对此,福尔摩斯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他说他不仅不知道日心说,而且即便知道也努力忘掉,因为大脑阁楼的空间有限,“只有傻瓜才会把他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破烂杂碎一股脑儿装进去。这样一来,那些对他有用的知识反而被挤了出来……”
旧知识太多,以致新知识无处放置,这种说法在认知科学上并不成立——事实上,研究显示,随着我们在某些领域的专业技能发展得更好,大脑记忆这些领域知识的能力也会相应增长。随着我们对记忆进行分类的效率越高,“大脑阁楼”的空间也会不断扩展。也就是说,学习越多,学习的能力也越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于童年早期的记忆如此之少,因为那时我们还不具备足够的人生经验对这些记忆进行分档和归类)。
但是,当福尔摩斯谈到要用合适的家具填充阁楼时,他的意思是小心选择你想要保留的以及你在生活中以备后用的某些经验、记忆和知识。因为我们选择什么,以及如何选择进入大脑阁楼里的东西,将决定和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比大脑阁楼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阁楼的结构,即大脑如何工作,包括它如何吸收信息,如何处理信息,如何归类、存储信息以备将来之用,如何整合抑或舍弃阁楼中已有的内容。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将我们的大脑划分为两个系统——系统1依赖情感、经验和直觉,它的速度很快,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和思考,而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做出反应;系统2则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做出决定,它比较慢,但更慎重、周密、有逻辑,因此在认知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比如,当你听到“粉红色大象”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对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反应是在大脑里出现一只粉红色大象的样子,然后你摇摇头,对自己说这不可能。这就是大脑的自然倾向:先相信,后怀疑。也就是说,先系统1,后系统2。
再来看一个例子:
1.球拍和球共计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是多少钱?
2.如果5台机器5分钟之内能制造5个小部件,那么台机器制造个小部件需要多长时间?
3.湖中有一片睡莲。每天,这片睡莲的面积都会增加一倍。如果这片睡莲能在48天之内覆盖整个湖面,那么覆盖半个湖面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不假思索,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0.10美元/分钟/24天。但如果你花一分钟时间思索,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在那一分钟内,你启动了系统2。
在《福尔摩斯思考术》中,康妮科娃将系统1称为“华生系统”,而系统2为“福尔摩斯系统”。
华生系统是一种懒惰而天真的思维习惯,它倾向于相信我们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信息。在这种操作系统之下,你任由世界不经过滤地进入你的阁楼空间,一切在某个偶然瞬间抓住了你的注意力的东西,将你的阁楼挤得乱七八糟。
相反,福尔摩斯系统则代表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倾向——对世界有着天然的怀疑和好奇精神。任何事都不能根据其表面现象来判断,每个念头、每次经验、每种预期都要经过仔细检查和思考,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也就是说,整个世界被默认为一个粉红色大象的世界。
其中消极与主动的分野,也就是福尔摩斯所说的“看”和“观察”的区别。
“看”是被动的,而“观察”则是积极参与。当我们无意识地看时,一连串的感觉输入不需要经过大脑的任何处理,只要睁大眼睛就行。我们不假思索地看,所以从周围的世界里吸收数不清的要素,却没能处理这些要素的深层含义。
有时候,我们甚至“看不到”摆在眼前的东西。“选择性无视”是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心理学现象——当我们太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