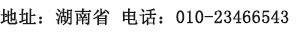特德·休斯(—),英国诗人,生于约克郡,剑桥大学毕业。他的诗集有《雨中鹰》()、《见见我的家人》()、《乌鸦之歌》()、《诗选集》()等。休斯的诗风格严谨,感情强烈,富于形象。大部分诗歌反映出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痛苦的感受。年1月6日刻有休斯生平成就的石碑被安置在英国威斯敏特教堂的诗人角。纪念碑与乔叟、莎士比亚、雪莱、狄更斯等人的墓碑比肩而立。
殉夫自焚特德·休斯
在你第一次死亡的神话里,我们的神就是复活了的你自已,这神圣的一位。我们日复一日的礼拜,伺侯你重生的白色产床,不愿响应的分娩,一心一意想要的生产,应当是此刻临盆的诞生。我们耐心等待。你精疲力尽的延长的阵痛给我们以献身的态度。假若三天里由于要生产,你在你身体上施加野蛮的动作,对着水泥墙猛撞你的脸,让你自已死掉(希望你死掉),你会变得怎样?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会受损伤,可能在死亡挣扎的怀孕期受伤害。我们的希望也泯灭,你表现的令人悲哀的痛苦也是快乐:你自己母亲的角色。我是助产士。日常生活的烦忙无非是毛巾、热水壶、里面没有麻醉气的橡胶麻醉面罩、你一直想得到的安慰剂,你像吞食可卡因似地把它吞下去。你的阵痛吓坏了你。肚里想要出来的东西吓坏了你。你不知道它会是什么东西--它却是你唯一想要的东西。一年年,一月月,一周周,夜复一夜,我躬身在那里,仿佛俯身于书页,哄它出世,用我的耳朵贴近你的肚皮倾听我们未出生的婴儿,倾听它的心跳,减缓你的恐惧。用催眠术按摩你入睡,对着那很快要落入我们的草帽的星宿低语,直至羊水迸发,我被感动得忘了自己。像我抗议、抵制的那样,我被席卷在洪水里,一阵新神话的雷鸣。我滚动在蛋白状粘液下面,瞥见你阵痛的呼喊像电影里的产妇一样,声音忽高忽低,这不是伴随滑溜溜香喷喷的新生女婴的哭声而呼喊,也不是伴随欢乐的哭泣而呼喊,而是伴随遥远的史前时期悼亡者的尖叫而呼喊。在死后,在我们的时代之外。印在录音带纹道里的呼喊此时此刻无法停止。你自己在火焰里生下了你。我们的新生婴孩是火焰中的你自己。那一条条火舌就是你的舌头。我爆发过尖叫,那是火焰。我想要说的是:“这些火焰是什么?”用我助产士的双手不是向火焰泼水,而仅仅是扑灭尖叫的火焰,尖叫使火焰愈烧愈旺,尖叫从火焰里滴落。我难以回避喷射火焰的火炬。你是火化柴堆上的儿童新娘。你的火焰依靠盛怒、爱和求助的呼叫而旺盛。眼泪是引火燃料。我是你的丈夫,在我们的新神话里扮演你父亲的角色(我俩浸有美国古老阳光的石油里,我俩被新生的大孩子所消耗),不是阳光的新生婴孩,而是黑暗里火焰和尖叫的大小孩把我俩的氧气吸光。
袁可嘉译
晨歌
西尔维娅·普拉斯
爱发动你,像个胖乎乎的金表。助产士拍拍年的脚掌,你无头发的叫喊在世界万物中占定一席之地我们是声音呼应,放大了你的到来。新的雕像。在多风的博物馆里,你的赤裸使我的安全蒙上阴影。我们围站着,墙一般空白。云渗下一面镜子,映出他自己在风的手中慢慢消失的形象,我比云更不像你的母亲。整夜,你飞蛾般的呼吸在单调的红玫瑰间闪动。我醒来静听:我耳中有个远方的大海。一声哭,我出床上滚下,母牛般笨重,穿着维多利亚式睡衣满身花纹。你嘴张开,干净得像猫的嘴。方形的窗变白,吞没了暗淡的星。而你现在试唱你满手的音符清脆的元音像汽球般升起。栖息着的鹰
特德·休斯
我坐在树的顶端,把眼睛闭上。
一动也不动,在我弯弯的脑袋
和弯弯的脚爪间没有弄虚作假的梦:
也不在睡眠中排演完美的捕杀或吃什么。
高高的树真够方便的!
空气的畅通,太阳的光芒
都对我有利;
地球的脸朝上,任我察看。
我的双脚钉在粗粝的树皮上。
真得用整个造化之力
才能生我这只脚,我的每根羽毛:
如今我的脚控制着天地
或者飞上去,慢悠悠地旋转它——
我高兴时就捕杀,因为一切都属于我。
我躯体里并无奥秘:
我的举止就是把别个的脑袋撕下来——
分配死亡。
因为我飞翔的一条路线是直接
穿过生物的骨骼。
我的权力无须论证:
太阳就在我背后。
我开始以来,什么也不曾改变。
我的眼睛不允许改变。
我打算让世界就这样子下去。
袁可嘉译
月球上的蜗牛
特德·休斯
月球上最悲哀的事情是蜗牛没有壳。你想找他,得先听他的哀鸣,摧心折肺的,听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扎穿。他奋力前进,那架势既严峻又缓慢。他悲哀,又湿又冷,如一滴巨大的泪珠嵌在薄薄的皮肤之间。他彷徨四顾,寻找一个遮阳的地方——因为第一道阳光就能将他融化,让他逃亡。所以,他只能在月暗面移动不止,肌肉的波浪翻滚,涎水横溢,月球上根本没有一个车库装得下这样一只蜗牛。他不是一般的庞大,身体两侧相距有一英里多的纵深,哪里能找到这么大的地方藏身。他非常痛苦,尽力伸长他的潜望镜,在月球黑暗的起伏中,摸索潜行。他找遍了月球的每一寸土地。我猜月表的银色,正是蜗牛的涎水的银白。杨铁军译
城市
特德·休斯
你的诗歌像一座黑暗城市的中心你的小说、你的故事、你的日记、你的信件,是这个庞大城市的郊区。旅店像市政厅一样通宵明亮挤满了学者、牧师、朝圣者。在夜里有时我驱车穿过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慢慢地开着车,仅仅是在我自身的黑暗之中溜达,回想着你所做的事情。我几乎总能一眼瞥见你——在某个十字路口,迷惑地盯着上空,60多岁。你被成堆的喧嚷包围。你一直站着。你的脸,在绿色或橘红色灯光之下是一片印度荒漠,狂野而不知所措。你想问些什么但你不能开口。你注视着每一张脸试图认出某个人。他们不理会你。而后光变红了他们都从你身边汹涌而去。而后你看见我在车中,望着你。我知道你在想:我应该认识他吗?我知道你在皱眉我知道你在努力去回忆——或者努力去忘记。
胡续东译
雨中鹰
特德·休斯
我陷入雨声阵阵的耕地,一步又一步
拔脚脱离土地之口的吞噬,
脱离那凭借坟墓的顽固习性
每走一步都没到我脚踝的泥土,但鹰
在高空从容垂下沉静的眼睛。
他的翅膀在失重的静寂中掌控万物,
在流动的空气中稳如幻象。
当狂风摧毁这些倔强的树篱,
按压我的眼睛,扰乱我的呼吸,攫获
我的心,
当雨劈砍我的脑袋直至骨头,鹰悬下
意志的钻石尖,如北极星
照引溺海者苦苦支撑:而我,
恍惚间被血淋淋抓住,土地口中
最后时刻充数的一小块食物,竭力走向
暴力的主支点,鹰悬停之处。
他也许是悠然自处时遭遇了
天气不测,为气流所害,一头栽下,
从他的眼中摔出,沉重的诸郡撞向他,
地平线将他捕获;那天使般的圆眼睛
摔烂,将他心中之血与大地的泥泞混合。
雷格译
蓟
特德·休斯
不顾母牛的橡皮舌头和人们锄草的手
蓟象长而尖的刀子捅入夏天的空气中
或者冲破蓝黑色土地的压力打开缺口。
每支蓟都是复活的充满仇恨的爆发,
从衰亡了的北欧海盗的地下遗迹
抛掷上来的紧握手中的一大把
残缺的武器和冰岛的霜冻。
它们象灰白的毛发和俚语的喉音。
每一支都挥舞着血的笔。
然后它们变苍老了,象人一样。
被刈倒,这就结下了仇。它们的子孙出现,
戴盔披甲,在原地上厮杀过来。
袁可嘉译
孩子般的恶作剧
特德·休斯
男人和女人的躯体躺着,没有了灵魂,迟钝地打着呵欠,愚蠢地凝视着,无精打采地呆在伊甸园的花丛中。上帝陷入了沉思。思考的问题非常重大,把上帝拉进了梦乡。乌鸦笑着。他咬着上帝唯一的儿子——蠕虫,咬成蜿蜒扭动的两半。他把蠕虫的后半段塞入男人的体内,带伤的一端悬在外面。他把前半段向前地塞进女人的体内,前半段向深处爬行,然后向上爬着,并从女人的眼里向外探望,叫唤后半段快点过来接合,快一点哪!因为实在痛苦。男人醒了,身体被拖曳着穿过草地。女人醒了,看见他正在过来。两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上帝继续睡着。乌鸦继续笑着。
吴笛译
马群
特德·休斯
破晓前的黑暗中我攀越树林,
空气不佳,一片结霜的沉寂,
不见一片叶,不见一只鸟——
一个霜冻的世界。我从林子上端出来,
我呼出的气在铁青的光线中留下扭曲的塑像。
山谷正在吮吸黑暗
直到沼泽地——亮起来的灰色之下暗下去的沉滓——的边缘
把前面的天空分成对半。我看见了马群:
浓灰色的庞然大物——一共十匹——
巨石般屹立不动。它们呼着气,一动也不动,
鬃毛披垂,后蹄倾斜;
一声不响。
我走了过去,没有哪匹马哼一声或扭一下头的。
一个灰色的沉寂世界的
灰色的沉寂部分。
我在沼泽高地的空旷中倾听。
麻鹬的嘶叫声锋利地切割着沉寂。
慢慢地,种种细节从黑暗中长了出来。接着太阳
橘色的,红红的,悄悄地
爆了出来,它从当中分裂,撕碎云层,把它们扔开,
拉开一条狭长的口子,露出蔚蓝色,
巨大的行星群悬挂空中。
我转过身
在梦魇中跌跌撞撞地走下来,
走向黑暗的树林,从燃烧着的顶端
走到马群这边来。
它们还站在那里,
不过这时在光线波动下冒着热气,闪烁发光,
它们下垂的石头般的鬃毛,倾斜的后蹄
在解冻中抖动,它们的四面八方
霜花吐着火焰。但它们依然一声不响。
没有哪一匹哼一声,顿一下脚。
它们垂下头,象地平线一样忍受着,
在山谷上空,在四射的红色光芒中——
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声中,在岁月流逝,人面相映中,
但愿我还能重温这段记忆:在如此僻静的地方,
在溪水和赤云之间听麻鹬叫唤,
听地平线忍受著。
袁可嘉译
特德·休斯是谁?在人们眼中,他是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丈夫,也是这段婚姻的背叛者。年,休斯与普拉斯相恋时,二人都刚刚进入诗歌圈不久,短短几个月后,他们便决定步入婚姻。在随后的几年间,休斯出版了处女诗集《雨中鹰》和第二部作品《牧神节》,奠定了他在二战后诗坛中的重要地位,普拉斯则以小说《钟形罩》收获声名。
几乎所有人都将这段婚姻视为两个天才的结合,然而,年,二人还是以婚姻破裂告终。次年,普拉斯在伦敦的公寓中自杀身亡,根据她死后被公开的部分日记和书信,这一悲剧的直接导火索除了她生前严重的抑郁症外,还指向休斯的出轨和家暴。这段轰动一时又惨烈收尾的婚姻将休斯推向了风口浪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研究者们不遗余力地从二人的作品中挖掘有关他们情变的线索,试图验证休斯在情感关系中的不堪,以致于远远超过了对他的作品本身的兴趣。
西尔维娅·普拉斯(左)与特德·休斯(右)
若简单地将对诗人的道德责难等同于对其作品的否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应当承认的是,休斯在创作上确有过人之处。作为战后寻求出路的人文思想者,休斯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