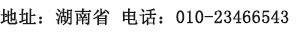临沂白癜风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bdfys/171021/5779693.html2.仪式至此,我已经尽力概括了对于非暴力抵抗要发挥作用来说非常基本的一些精神特性和实际步骤。但是仍然存在两个基本疑点,在东方和西方,不但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就是许多支持者也在唠叨:如果这样一种器具所需要的精神能量靠的是禁欲——而且似乎甘地至少对他自己和他的一些亲近追随者坚持说是这样——那么这种真理多大程度上能被过着本能生活的凡夫俗子所掌握,它又多大程度上与普通人“本能的”好斗习性格格不入?一句话:它多大程度上是自然的?为了合乎自己继承的宗教,甘地不能忍受对动物的任何有意伤害。然而,从文化水平上来说,他属于那种普通的达尔文主义者,这一名目本身就包含了相当的矛盾心理,因为它使得人成了被认为在控制本能方面远不如人的那些生物的“后裔”。有一次甘地访问伦敦,应邀对美国人讲几句话,甘地在广播演讲中说道:“迄今为止,国家之间都是在以野兽的方式相斗。”他把这种方式具体说成“施行报复”,并宣称施行报复是“支配着野兽的法则……与人类的尊严不相符”。现在,鉴于我们从那时起获得的动物学或人类的知识,我们不能继续断言缺乏自我控制的人“不如一只畜生”,除非其含义是——以生物的规范来衡量——他很坏很坏。不过,必须记住,只是在后达尔文主义时期,人类才开始面对这种令人震惊的知识:即他可能仅仅是某一特别种类的哺乳动物。承受这种震惊是达尔文之后一个世纪的任务,这就轮到甘地的同代人弗洛伊德(他喜欢爱恨都很真诚的气度不凡的狗,倡导对性的一种睿智的接受)来说:“大体上,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已经解决,诉诸的是暴力手段。这与动物世界的情形是一样的,人类还不能说自己排除在外。”弗洛伊德由此得出了那个严酷的结论,即在人这里“屠杀敌人可以满足本能的渴望”。但是当他说他赞同“人对人是狼”这一古老的格言时,人们至少想知道他指的是人对人是像狼对人的样子,还是像狼对狼的样子。不管怎样,考虑到这两个人发明了以非暴力对付我们的本能的两种类似的手段,那么就不能否认这种后达尔文主义代表着最低的共性。这是即使最伟大的人在想象他们的时代时也有局限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卡纳德·罗伦兹的《论侵略》一书可能是已知的对同一物种的某些高等动物侵略的最好总结。当然,这些动物在猎食的时候,在准备解决领地争夺问题的时候,或者在受到强敌觊觎的时候,会展示出无穷尽的富于技巧的暴力。很明显,该攻击时攻击,该防御时防御,这对任何在与同类协调、与他类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的关系中占据并活动于某些空间中的动物来说,一定是本能的行为。问题是:何时何地“天生的”侵略性会变成狂乱的暴力,击杀的本能技巧会变成无谓的凶杀?印度有些丛林里的土著在他们的地区与“野兽”面对面地生活在一起;但是甚至他们都认为,老虎中偶尔出现的“杀手”完全可能是个亡命之徒或者异常者,人不可能与之达成妥协,因此必须将之挑出来猎杀。然而,一只正常的狮子,在它准备捕食(它只在饿了的时候才这么干)时,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恼怒或狂怒的迹象:它只是在“干自己的工作”,或者看上去如此(当它的表情能在野外通过长焦镜头观察到时)。在自然的簿册上,没有任何集体歼灭的普遍趋势——除了,显然,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在特别的条件下会有。狼群在追赶畜群的时候并不会大量杀死健康的牲口,而只是挑选出那些落伍者。在它们内部,它们可以形成忠实的友谊;据报道,当两只狼偶然发生搏斗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瞬间,就是当其中一个力不能支而将未受保护的脖子暴露给对手的时候,对手反而本能地不去利用眼前的这个“非暴力的”情势。这种本能的和平习性的一个更为仪式化的详尽展示出现在北方雄鹿的角斗比赛中。这种比赛开始先是一段炫耀:两只雄鹿并排向前小跑,上下挥舞着它们的鹿角。然后,它们就像接到命令似的突然停了下来,呼的转过身来以一个适当的角度对峙,它们把头低得直到鹿角几乎触及地面,然后噼啪作响地互相攻击。如果碰巧有一个转身比另一个早,因此得以用它那有力挥击的又重又尖的鹿角威胁对手全无防护的侧腹,它会立即制动它过早的转身,加速它的小跑,继续并行前进。直到双方都准备好了,跟着就会发生完全的相互对抗,一场有力但没有伤害的角斗。胜者是能够持久的一方,而败者通过一般不再攻击胜者的仪式化脱离,承认比赛失败。罗伦兹说,在高等动物中有数不清的类似和平仪式;但是他也指出(对我们最为重要),任何时刻的去仪式化都会导致致死的暴力。人们曾经发现过鹿角死死缠在一起的两只雄鹿的骸骨;但是它们不过是本能仪式失败后的牺牲者。我们将这种观察不仅归功于那些把我们的摄影视线伸展到动物领地的新技术,而且归功于观察者一方乐于让一些动物在它们自己的生活领地安居,或者在进入动物的领地时,所带的防卫装备绝不超出适当的范围——被观察的动物不会把他们的出现当成任何别的,而只是看成一种非暴力的接近。然而,这样的一位行为学家,他所丢弃的并不只是过分的恐惧。他接受一个包括动物在内的万物一体的宇宙超越了所有关于人类地位下降或上升的问题——更不用提人的屈尊俯就,这样就清楚了,归之于动物的一些侵略性的或可怕的行为,其实反映的是人的偏见、感觉的外化和恐惧。我们从这种观察中了解到,“侵略性的”行为是在一定条件下被引发和终止、转移或替换的。因为,就像罗伦兹如此有特性地说的,“是的,确实,驱力可以被驱动,本能可以被煽动”——即,通过强制性的环境。同样的原因,一种驱力也可以一直潜伏,而一旦受到刺激马上化为有力的行动。人们可能要想,这就使得解释动物的侵略性没有必要运用弗洛伊德式的本能模式(如我所料,罗伦兹这么做了),这种模式基本上是从性中发展出来的——而人的性比起动物的性,是一种更普遍、更深入、更自发的驱力。“本能”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词汇。生物学家正打算丢弃它,不过在精神分析那里还不可缺少。当人们在太多生物学的含义上使用该词的时候,很容易暗示出并不是他本意的东西。侵略中包含某些出于直觉的东西、某些来自天性的东西,但人们并不怎么愿意把侵略称为一种“本能”。然而,如果人们把这个词完全丢弃,那又忽略了人的行为中积极有力和受驱动的方面。问题的症结在于:弗洛伊德所说的Trieb是个含义介于英语的“驱力”和“本能”之间的词。比较动物心理学家的陈述和精神分析学家的陈述时,问一下“本能”一词指的是某种天性(instinctive,一种先天的适应能力的模式)还是某种直觉(instinctual,一种驱力或受驱使的东西,不管是不是适应性的),总是很管用。如果为了比较的目的我们保留“本能”这个词,那么现在清楚的是,动物的侵略行为以及和平花招都是天性的——即,这是事先形成的行为模式,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使一些准备就绪的驱动能量得到瞬间、有力和熟练的释放。对于动物来说,这就使得它完全不必过于兴奋,也不必用任何个体的或“道德的”风尚来抑制自己。因为,仪式化确保事先就要选择两个大致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样的对手被同等地赋予了精确地展示整个一套预定的和互惠的反应的能力,它们也都同样会令人信服而有效地承担最终角色(我们称为胜利者或被征服者)中的任何一个。动物侵略中的大部分东西都已经这样“仪式化”了,朱廉·赫胥黎(JulianHuxley)首次表述了这一点。譬如海鸥的怒鸣等行为若不是一种本能的“惯例”,并且只投入了相对很小的一点驱力和感情(除非发生了一次“事故”),那么它们早就焚毁于自己的激情中了,而我们也就绝无可能见到怒鸣的海鸥。像罗伦兹那样,人们在这种仪式化中完全可以看到对不当暴力的道德抑制这一人类的先天习性的一个进化意义上的先例;人们(我就是)也完全可以走得更远,在甘地的非暴力抵抗中看到某种和平对抗的迹象,这种和平对抗可能不仅植根于人的宗教虔诚,而且植根于在一些“野兽”中也已经很常见的天性模式。不过,我们之所以说这些,却绝不是号召人类径直回归自然。我们所说的毋宁是这样一个实例,就是人类有能力以灵感、洞见和信仰“治愈”他的直觉情结,并在人的水平上恢复动物身上如此无心却又如此重要地被赋予的东西。弗洛伊德就是因为这个才能够说当动物的环境相对它的天性适应能力改变得太快、太剧烈时,动物就会毁灭,而人类,作为自己环境名副其实的制造者,将因无谓的直觉需求而毁灭。人类这样就能把自己吃死、喝死、抽烟抽死、干活干死、“爱”死、骂死、吹捧死、奉献死。因为人类的直觉力量从未完全约束在适应或适当的模式之内;这种力量有些被压制了、转移了、歪曲了,却又经常从压制中返回来激起完全是人类特有的焦虑和愤怒。这里必须承认,甚至甘地简化饮食的狂热尝试,不管其中的顾虑有多少说教成分,也确实同时包含了一个通向弗洛伊德的洞见的真理。如果觅食的本能,比如说,引导动物找到和吃掉足量的适当食物,这与人类山吃海喝的直觉活动完全不同,这种直觉可能使人将他的资源的很大部分花在烈酒和汽水、香烟和咖啡上,远远高出花在子女教育上的。这样,就有了甘地对人有一些无用的驱力、人需要设法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人类的未来很重要。问题是我们将怎样处理这种意识:是重申旧道德(但是这些旧道德,如甘地在自己的一生所证明的,有着与它们要限制的驱力一样过于泛滥的趋势);还是力争一种建立在新的洞见基础上的新伦理?不管怎样,弗洛伊德原本谴责的只是人对拷打和杀死敌人的快乐的“直觉”渴求(虽然他被人译做谴责的是“天性的”东西)。然而,此中,我们必须再次面对文明化的人在某些方面如何比动物还沉沦,很可能比他的先祖还低劣:因为文明化的人、道德还有所有一切正是或者已经成为,用罗伦兹可怕的短语来说,宇宙中的毁灭性因素。那么,问题就是,所有种类的暴力,即以非理性的狂怒为特征的、以大暴乱为特征的或者以彻底灭绝为特征的暴力,能否完全追溯到我们的动物本质——或者,还能追溯到我们的原始祖先。电影《死鸟》用了不起的美学技巧展示了本世纪才在新几内亚高地发现的两个部落如何沉溺于一种定期的、仪式化和戏剧化的战争,他们身穿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士羽衣,在指定的战场相互对峙,轮番猛烈地进攻或喧闹地撤退。这些部落有许多很邪的仪式;他们公然炫耀阴茎,他们切断妇女的手指,看了让人既恶心又畏惧。但是,尽管对武力如此着迷,却没有任何消灭、镇压或奴役的企图;尽管在炫耀阴茎时一定会大声羞辱对方,这些部落也肯定把某种战争惯例维持了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在这种惯例中,可以放心敌人会遵守一定的仪式化,这种仪式化使得双方只会为尚武风气牺牲极少数的几个人。这里,几乎可以认定存在某种文化上的安排,它介于天性和直觉之间的某处,同样也介于部落自立与部落联盟之间的某处。这种战争好像代表着人类的一种潜能;假如可以说动物中的“仪式化”会帮助参与者澄清情势的模糊之处并恢复天性的信任,那么人类仪式化的要旨很可能就是通过定期解决由划分假种而引起的矛盾来恢复和平。尽管当甘地觉察到有必要把军人的一些纪律转移到激进的非暴力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意识到了传统战争存有某种仪式的可能,但是必须承认,把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械化杀人战场,希望他们偏偏在那里学到非暴力抵抗所需要的勇敢和侠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自从我们与外人发生战争、与自己人发生战争(现在仍然如此)之时起,我们就已经明白了如下道理:即便人类战争总是包括某种一致的仪式,英雄由此为幸存者、为理想化共同体的不朽而牺牲,但是人类的技术发展已经把战争曾经可能具有的任何调适价值远远地抛在后面。今天我们知道下述所有的方面都在发展变化,因而必须放在一起研究:社会认同和对“非我族类”的敌视,道德和正义的暴力,发明创造才能和集体杀戮。从人手射出的箭镞,到洲际导弹发射的弹头,人由富有正义且技艺高超的进攻者,已经变成了一个技师,他能通过瞄准器或者在地图上把对手看做只不过是一个目标,或者看做种族屠杀中的一个统计数字。年,皮耶拉尔在《政治家》上撰文讲述,在离生命终结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外国记者问甘地:“您怎样用非暴力来对付原子弹?”他回答说:“我不会躲进地道,我不会躲进隐蔽处。我会走到空地上,让飞行员看到我对他没有一点恶意。我知道,飞行员在那样的高空看不到我们的脸。但是我们心中的渴望——他不会来伤害这个——将会直达他那里,他的眼睛会因此而睁开的。”愚蠢透顶?可能是吧;不过,或许是真的,正因为它的荒唐。因为甘地的回答只是把一个基本的非暴力态度戏剧化了,尽管必须承认这种态度在电子和核的时代得寻找新的方式,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人类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已由圣雄在他的时代和环境中施行了,并证明是可行的。至于说到未来,难道那种给人类提供自焚手段的技术,没有同样提供给他相隔无限的距离也能看到自己同类的方法吗?难道他没有同时获得一种新的内省方法去面对自己,因而面对自己心中的所有他人、面对他人心中的自己?如果我们补充说人类必须学会像他面对所有别的一样面对自己,我们是在暗示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竭力不去正视人类也只是一个物种。如果我提到过与此有联系的人类的“假种”心态,这个概念却诱导罗伦兹将“假种形成”(pseudo-speciation)这一术语归之于我,不过我倒乐于笑纳。但是,“假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人类明显属于同一个物种,但却是分为不同的群体(从部落到民族,从种姓到阶级,从宗教到意识形态)出现并持续下去的,各种群体带给它的成员独特而优越的身份以及不朽的一种坚定意识。然而,这就要求每个群体在宇宙的正中心为自己虚构一个位置和时刻,而一个特别有远见的神正是在此时此地将它造得比所有别的那些凡人都要卓越。人们可以远溯史前时期,想象当时的人类,从自然标记上看,他们是最为裸露、最少特征的动物,尽管具有自我意识,但是缺乏同属一个物种的认同。他可以用羽毛、兽皮和颜料把自己装饰得鲜艳夺目,把自己这一伙抬升为一个神话中的种类,随便称做他为“这些人民”取的什么名字。从最友好的方面来说,“假”的意思只是将某物乔装成不是其本来所是的样子;而且,以其假种的名义,人确实可以给自己和自己的世界赋予工具和武器,角色和规则,赋予传说、神话和仪式,这样就可以把自己这一群团结在一起,并将诸如激发忠诚、英雄主义和诗意这类超个人的意义赋予它的存在。人们可以设想一些部落和文化曾经长期和平地培育的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然而,使得这个“自然的”过程成为一种全方面的潜在邪恶的东西却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发生险恶变化和突然动乱的时候,认为自己是最杰出的种的想法一定会由于对其他假种的极端恐惧和仇恨而得以加强。因此,这些其他假种,必须通过定期的战争或占领、通过严厉的立法或当地的习俗,予以消灭或者限制在“他们的地方”——这就成了人类的一个定期的、经常是相互性的强迫症。至于最不友好的方面,“假”指的是某人尽力用宣传中半真半假的内容来愚弄别人也愚弄自己;恐怕我想说的正是这层意思。人类集体认同中的这一“假”的方面在历史和经济更替的影响下会占据上风,进而使得一个群体的自我理想化变得更具防御性并且更加排外。这个过程对人类来说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像现代历史表现的那样,这种假种心态甚至拒绝屈服于进步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果实。甚至最“先进”的国家也会怀有、实际上是疯狂地表现出,对假种心理的一种微妙的支持。这种心态在一个开明的现代国家完全胜利的例子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然而,假种形成最骇人的方面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种”如果被另一个所统治,它就很容易把占统治地位的“种”的嘲弄性看法吸收到它的自我评价中,这就是说,它允许自己被当做幼儿看待,同时它在内心积聚起一种愤怒,它不敢向压迫者发泄这种愤怒,实际上经常是想都不敢想。这会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祸根,先是带来被压迫者自己内部偶尔的暴力,直到最后,当历史环境似乎要求并支持来一次爆发的时候,所有积存的愤怒将在一刻间宣泄出来。这样的放纵即使在大肆破坏的时候也会有孩子般的快乐,这一点不应使我们惊讶:因为被压迫者在经受压迫时,仅仅在他们的个体生命中培养了一种防御性的天真和幼稚,在他们的文化遗产中培养了一种破碎的原始状态。因而,以下说法就经得起推敲,这即,哪里对假种的强调颇为流行——就像大部分殖民历史中表现的那样,——哪里每个参与的个体的发展就会受到各种各样内疚加愤怒(这种内疚加愤怒会阻止真正的发展)的威胁,即便那是一个富于知识和技能的地方。然而,历史提供了敌对群体可以解除其假种心态的一种方式,这就是经由某一更广泛的认同。这一点可以通过领土统一实现:和平时期的罗马帝国就囊括许多种族、民族和阶级。整体“交通”中的各种先进技术也统一起来:航海、机械化运输和无线电通讯帮助推动了各种变革,最终也包容了某种日益广阔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有助于克服经济恐慌,克服对文化变动的焦虑和对精神真空的担忧。我们在甘地的人生发展中已经看到这种更具包容性的认同之一具有的强烈吸引力:这就是成为大英帝国的一名开明公民。在证明自己既不愿抛弃与本国传统的血肉联系,又不愿轻易牺牲对他帮助击败英国霸权的能力最终有所助益的西方教育——在所有这些表面的矛盾中,甘地表现出对他的时代的现实了如指掌。因为在世界各地,现在奋斗的目标是更具包容性的认同的预先发展。那么,我认为,甘地在对历史现实的巨大直觉中,在他担当“行动中的真理”的倡导者的能力中,可能已经创造了一种仪式化,通过它,兼具现实态度和精神力量的人们,就能够用一种与动物和平仪式里固有的本能安全设置类似的互相信任来彼此面对。为了不再沉迷于更深的思索,让我回到所研究的具体事件,勾勒出事件与方才描述的和平的仪式化模式的某些契合之处。在阿赫梅达巴跟在其他场合一样,甘地远不是等着受攻击以便他能够“消极地抵抗”,他径直迎上对手,宣布冤情是什么以及他将采取什么行动:在限定的范围内打交手战是他的方法的精髓所在。这样,他就给对手以最大的机会来作出知情的反应,如同他把自己的要求建立在对事实的彻底调查上。他告诉工人们所提要求不要超出公平适当的限度,但同样宁死也不能降低要求。他也注意问题务必由双方平等地参与解决。他解释说,工厂主的资产(资金和设备)与工人的财产(工作的能力)相互依存,因此,在经济力量和尊严方面是对等的。换句话说,他们分享同一个包容性的认同,他们可以说是同一个种。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允许任何一方损害另一方;即便工厂主变得恶毒,变得有威胁性,他也禁止工人们反过来威胁他们。他坚持要求这些挨饿的人们立誓不搞任何破坏,甚至也不得破坏对手的声誉。这样他就不仅不允许对机器或人(记住,警察从罢工第三天起出来就不带武器了)进行有形的伤害,而且不允许以道德谴责引起对手的愤怒——连同指责者的内疚感。接着,他不允许人在分化为假种的过程中特有的坏良心、反面认同和伪道德的渐次恶化。事实上,他承认工厂主们的错误仅仅是由于他们对自己和工人们的义务和作用有所误解,他呼吁他们的“更好的自我”。在这样表现对他们绝对信任的过程中,甘地愿意随机而动,而这导向这样一种互动,即从对手那里而来的线索决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尽管他从来不愿利用对手一方突然出现的任何弱点。对受难的接受,事实上,对死的接受(这对他的“真理的力量”来说是最基本的),形成了一个无须向任何人屈服的主动选择:它包括接受认为是自己招来的惩罚。所有这些既是一个无意伤害他人的宣言,同时又(这里与罗伦兹雄鹿的例子相当对应)表达了对对手不会执意伤害他人以致超过一定限度的某种信任,当然,对手这种行为的前提是,他确信自己非但没有处在丧失认同或合法权力的巨大危险之中,而且事实上还可能获得一个更为包容的认同和一份更为长久的权力。这样的信任,如果被辜负了,将会导致一切东西的丧失——权力、脸面、生命——但是原则上说,非暴力抵抗者更愿意选择死亡,而不是谈判、妥协、再谈判、再妥协,那最终总被证明是后来冲突和杀戮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根植于某种在场和